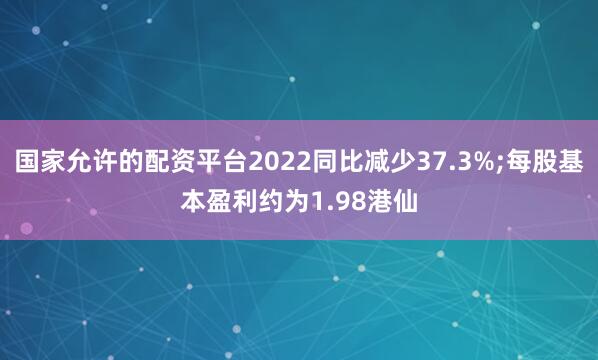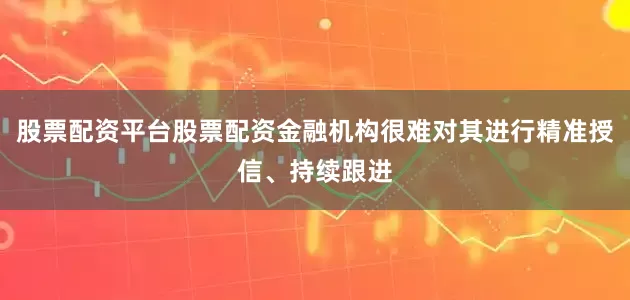你敢相信吗?那个在2005年,站在纽约纳斯达克交易所中央,意气风发地敲响上市钟声,让整个华尔街为之侧目的中国人,仅仅在几年前,还被日本索尼的高管像赶苍蝇一样,挥着手从会议室里轰了出来?从被视作尘埃,到成为全球科技巨头的座上宾,这中间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藏着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叫邓中翰。2005年,他创立的中星微电子在纳斯达克敲钟,成为中国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芯片设计公司,风光无限。然而,时间倒回几年,画面可就没这么体面了。当时,他带着团队和呕心沥血研发出的第一代芯片,满怀希望地走进索尼公司的大门。可会议开始还不到五分钟,他那句“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团队”才刚开了个头,就被对方一位主管极不耐烦地打断了。那位主管甚至连正眼都没给他一个,只是轻蔑地摆了摆手,说:“索尼是技术的源头,我们没兴趣听什么产品推销。”
那轻描淡写的一挥手,对邓中翰和他的团队来说,不亚于一记响亮的耳光。手里紧紧攥着的那枚小小的芯片,瞬间变得无比沉重,心里那股火,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气炸了,更何况是邓中翰。要知道,在回国创业之前,他的人生剧本简直就是开了挂。这家伙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在世界顶尖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别人读一个学位都费劲,他愣是在五年内,同时把物理学硕士、电子工程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三个硬核学位全都揣进了兜里,这在伯克利建校史上都是蝎子拉屎——独一份。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进了蓝色巨人IBM,搞的是最尖端的高端芯片研发,手里攥着好几项美国核心专利。后来他自己下海创业,公司做得风生水起,市值一度冲到1.5亿美元,连芯片霸主英特尔都眼馋,想来投资分一杯羹。百万美元的年薪,上不封顶的研发经费,硅谷的阳光和别墅,这本该是他一帆风顺的精英人生。
可命运的齿轮,总在不经意间转向。1998年,他回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周光召院士在会上的一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他的心里:“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产业,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颗种子,就这么悄悄埋下了。一年后,他受邀回国观礼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当看到我们自主研发的歼-10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天安门广场时,他激动得彻夜难眠。一个念头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战斗机造得再漂亮,如果里面的“心脏”——芯片,是别人的,那不就等于一把没有开刃的宝剑吗?关键时刻,人家随时能让你变成一堆废铁。

那一刻,硅谷的豪宅,华尔街的追捧,百万年薪的支票,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朋友都大跌眼镜的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回国。
他找来了几个在朗讯、惠普等顶尖公司工作的老伙计,一头扎进了北京中关村一个一百多平米的半地下仓库里,“中星微”这艘小船,就在这简陋的环境里扬帆起航了。理想是星辰大海,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一记重拳。创业搞芯片,设备是第一关。他们想从国外买点先进的设备,结果对方一听是中国公司,直接两个字:“禁运”,理由是“涉及敏感技术”。设备买不来,那就招人吧。他们跑遍了全国的大学,最后也只招来了12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信息产业部给的一千万启动资金,在烧钱如流水的芯片行业里,很快就见了底。最惨的时候,公司账上就剩下三万块钱,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更要命的是,当时的中国大陆,连一家能拿得出手的芯片制造厂都没有。就算你把芯片设计得天花乱坠,也得低声下气地去求港台的代工厂给你生产。巨大的压力下,团队里有核心成员扛不住了,私下劝他:“老邓,算了吧,回美国去,凭你的本事,在哪儿不是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在这儿活受罪?”邓中翰当时眼睛都红了,他拍着桌子吼了回去:“核心技术这玩意儿,是求不来的,也买不来!我们今天要是撤了,那中国的芯片就真的没指望了!”

他带头把自己在美国攒下的一百多万积蓄全部投了进去,其他几个创始人也一咬牙,把父母在北京养老的房子都拿去抵押了,硬是凑了五百万救命钱。那段日子,十几个人就像住在山洞里的野人,吃喝拉撒全在那个阴暗潮湿的半地下仓库里。24小时三班倒,困了就在行军床或者地上躺一会儿,饿了就抓起一包泡面。没有现成的技术参考,他们就去市场上买来英特尔的芯片,然后用化学溶剂,像做手术一样,小心翼翼地把芯片的封装一层层腐蚀掉,露出里面密如蛛网的电路。然后,十几个人就轮流凑在高倍显微镜下,一根线一根线地看,再用手把上万张复杂的电路图给硬生生地画出来。
有行业专家后来评价说,这种反向工程的法子虽然“笨”,但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它不仅是在复制,更是一个深度学习和解构的过程,硬是让他们把国际巨头的技术逻辑给摸了个底朝天。硬件设备跟不上,他们就在设计上下功夫。比如,别人需要一千个晶体管才能实现的功能,他们就绞尽脑汁地优化算法和架构,想办法用八百个甚至更少的晶体管搞定。这种“巧劲”,硬生生弥补了制造工艺上的巨大差距。

2001年3月11日,一个注定要被载入中国科技史的日子。在那个半地下仓库里,“星光一号”诞生了。这是中国第一颗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消息一出,整个科技界都为之震动。这枚小小的芯片,在当年的年度国家科技成果评选中,与“神舟二号”载人飞船、水稻基因组测序这两项国之重器并列,成了三大科技成果之一。
然而,芯片造出来了,卖给谁又成了新问题。这才有了文章开头,在索尼公司被无情羞辱的那一幕。那口被噎住的恶气,反而成了整个团队最强的催化剂。他们憋着一股劲,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对芯片进行了疯狂的迭代优化,硬是把功耗又降低了三成,性能提升了两成。到了2003年,“星光五号”芯片横空出世,其性能和稳定性,已经完全有资本跟国际巨头掰手腕了。这一次,不用他们再去敲门推销,苹果、三星、惠普这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国际大厂,主动为他们敞开了大门。很快,全球个人电脑的摄像头里,开始跳动着一颗强劲的“中国芯”。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邓中翰很早就意识到,未来的竞争,绝不仅仅是单个产品的竞争,而是标准和生态的竞争。在占领了PC摄像头芯片市场后,他带领团队牵头制定了中国自主的安防监控视音频编解码标准——SVAC国家标准。这意味着,他不再只是一个产品的制造者,而是开始成为规则的制定者。2016年,他们又发布了全球首颗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星光智能一号”,功耗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一半,提前卡位了人工智能赛道。有专家评价说,这种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和核心芯片双重自主可控的战略价值,不亚于一件“小型核武器”,能在关键时刻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如今再看全球芯片格局,早已不是当年一边倒的局面了。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到2024年,中国大陆晶圆厂的全球产能份额已经超过了20%,在一些关键制程技术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反观美国,自从2018年开始挥舞制裁大棒,反而导致其本土芯片企业在华市场份额不断萎缩。虽然他们在顶尖设计领域仍有优势,但在许多细分赛道,中国已经从过去的“跟跑者”,变成了“并跑者”,甚至在某些领域实现了局部领先。
从那个阴暗的半地下仓库,到纳斯达克的钟声,再到今天AI芯片领域的领跑者,邓中翰和他的团队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一条无比崎岖却又无比坚实的自强之路。
这条路,不是靠谁的施舍,也不是花钱买来的,而是一代科技工作者,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用自己的头发、汗水和不屈的脊梁,一点一点铺出来的。
(免责声明)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无低俗等不良引导。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
证券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股票开户哪一家比较好自去年“9·24”行情启动以来
- 下一篇:没有了